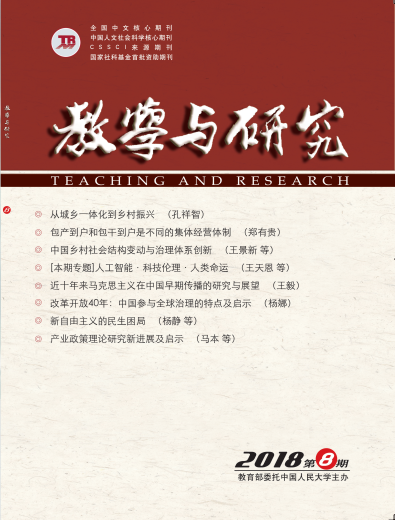为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沟通、融合,“‘对话《资本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新时代’学术论坛”第1期暨“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青年学者论坛第19期”于2018年4月1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会议由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哲学研究》编辑部、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人民大学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高精尖创新中心主办,《教学与研究》编辑部协办。来自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经济学等学科的专家学者30余人与会。论坛的宗旨为:对话经典、多维阐释,跨越学科、融合视域,根植理论、观照现实。
与会学者普遍认为,新的时代条件激活了经典著作研究的时代性问题意识,使得我们与《资本论》的当代对话成为可能。原著研究不能仅仅停留于文献梳理考证或个别社会问题、时髦热点的牵强比附,而要发掘时代的根本问题,将之提升到哲学问题的高度,并以此来激活《资本论》及其手稿。与会学者围绕“《资本论》研究与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资本论》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范式’”“《资本论》研究与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资本论》研究与哲学、政治经济学的对话融合”等议题展开了充分深入的研讨。
一、《资本论》研究与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
与会学者围绕《资本论》这一经典著作,深刻把握时代脉搏,针对传统的研究方法进行当代反思,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研究视角、路径与方法。
学者们强调了推进《资本论》研究对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重大意义。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聂锦芳教授指出,作为一位思想家,马克思观点的复杂内涵并不在于他明确的表述,而在于他对自己观点的探索和论证。马克思将自己的毕生心血投入到对资本的研究中,并随着时代的进步不断地修正自己的理论框架,留下了以《资本论》为代表的一系列丰硕的思想成果。只有把马克思悉心研究资本的全部经历和思维方式作为我们理解马克思的基础,才能更好地推进《资本论》研究的发展并彰显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科学性和生命力。在学术研究和理论探索的过程中,每一代人都有自己不同的学术视野、知识背景、解释思路乃至观点体系,每一代人也都要面对和解决自己所处时代的不同现实问题。当今时代的青年学者们应静下心来与原典对话,拒斥盲目追随时尚和潮流,真正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展开深入的沉淀式研究,努力发掘原典的当代启示与价值,最终实现对现实问题的积极回应、对未来发展的正确把握和对前人思想的有效超越。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侯衍社教授认为,马克思以别人不具备的锐利眼光发掘时代的弊病,揭露出资产阶级剥削广大劳动人民的秘密。马克思的《资本论》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芒,从不同的学科角度深入探讨这一著作中博大精深的思想,对于推动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还有学者阐明了对话《资本论》对于思考新时代问题的重要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哲学研究》主编崔唯航研究员指出,此次论坛的主题包含三个意义重大的关键词:第一是“对话”。哲学生于对话,死于独白。随着当下实践活动日新月异的发展,理论研究和探索中所激发出来的有价值的思想却尤为稀少,思想资源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稀缺和最珍贵的资源。对话探讨的学术形式兼具表达思想和激发思想的双重功能,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应不断强化对话意识。第二是“新时代”。继黑格尔提出哲学是“思想中所把握的时代”之后,马克思进一步将哲学阐释为“时代精神的精华”,表明哲学具有把握时代脉搏、反映时代规律、聚焦时代实践、回应时代问题的思想特性。学习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如何把握他们所处时代的现实,对于我们思考新时代的现实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三是“《资本论》”。资本作为渗透到时代的每一个角落和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的主导力量,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仍是活生生的现实存在。要认识、理解和把握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就离不开对资本问题的考察,离不开马克思研究资本问题的集大成之作——《资本论》。
学者们分别从经济学和哲学角度对《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研究目的进行了重新思考。中国人民大学谢富胜教授结合新时代的生产方式,对《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提出了一系列新见解。他指出,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探讨生产方式指的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关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核心,他认为并不仅仅是强制下的劳动榨取过程,同时也是强制与同意的特殊结合。谈到资本循环与资本积累,他从生产与价值增殖的角度指出,劳动过程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核心运作逻辑的承载领域——是剥削和剩余价值的创造。另外,他认为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本身又创造着跟它本身趋势相对立的经济障碍,使得使用价值的生产与价值的实现之间的矛盾始终存在,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在消除这种矛盾的同时,也改变了劳资关系的具体形式,逐渐形成新的积累体系。中央民族大学刘梅博士探讨了《资本论》的研究对象、辩证法及其“隐匿现实”之间的关系问题,重新阐释挖掘《资本论》所包含的丰富的理论内涵。她认为《资本论》的研究对象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并无二致,但在深层次上,马克思已经转向了具有无限丰富的感性体验的“人的事实”,见“物”的同时也见到了“人”,即从知性思维走向了辩证法。但同时,她认为不能仅仅把资本运动过程中的内在规律和必然趋势抽象为一种资本的逻辑,更应该透过资本逻辑深入把握其在社会中的现实展开,对《资本论》的解读必须超出现有的经济学和哲学视域,在更加广阔的理论视野中去完成。最后,她认为《资本论》的写作目的是为未来社会奠基,其经济学研究只是表象,而政治哲学才是本质。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资本主义批判,使得作为新形态的共产主义成为现实,是《资本论》中的一个隐而不显的隐匿现实。
二、《资本论》研究与马克思主义
哲学研究的“新范式”
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故步自封的理论体系,而是善于创新、善于包容的思想有机体。对马克思经典著作的研究永远没有盖棺定论,任何进步的思想都会被囊括其中。学者们普遍认为,《资本论》研究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式转换”、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新范式”具有关键性的意义。通过反思《资本论》的传统解释模式,他们尝试分析《资本论》的深层次哲学内涵,提出了一系列新视角、新观点与新问题。
学者们认为,要突破“《资本论》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简单应用”的传统解释模式,必须通过深入把握《资本论》的理论逻辑来对历史唯物主义形态进行当代建构。中国人民大学郗戈副教授认为,传统解释模式将历史唯物主义现成地套用到《资本论》上,从而遮蔽了《资本论》对马克思哲学的创新发展意义。应当从《资本论》的理论逻辑自身出发,内在地阐发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充分展现其内在张力、思想深度与生命活力。首先,《资本论》不是对现成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简单应用和验证,而是从“三重批判”即资本逻辑批判、物象化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中内生出历史唯物主义新形态的建构。三重批判构成了对现代社会结构的共时性再现。这种共时性再现凸显了社会结构诸层面之间的复杂交织与丰富互动,呈现为一种批判与建构相统一的理论总体性。进而,《资本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建构,意味着历史唯物主义自身的充分“历史化”,并发展出一个扬弃了抽象原理的具体理论总体。最后,马克思共时性的结构与历时性的分析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体,具有新世界观建构的意义,即不仅仅对现代世界的根本存在方式进行研究,而且还包含着对现代世界的生成方式、内在超越方式的再现,因而是改变世界的世界观。
还有学者探讨了《资本论》的辩证逻辑问题。关于资本自身展开的逻辑,首都师范大学黄志军副教授以《资本论》第二卷为研究对象,探究资本的自我创造和推动过程。他认为,《资本论》第二卷以资本的循环过程为主要研究对象,只有在这种流通中才能表现资本自身展开的逻辑。他以《资本论》第二卷的展开逻辑,对资本内部的辩证过程展开探讨。首先,他认为理解资本循环的基础在于货币的“复归”,表面上是货币的自我推动和创造,但本质上货币的“回复”已经不再是原有的货币形式,而是货币资本。其次,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对于价值转形问题的研究进一步揭示了资本内部的辩证法,并说明了资本辩证运动的内在驱动力和基本运行方式。最后,针对社会资本如何实现再生产的问题,他指出马克思一方面揭示了个别资本与社会资本之间的辩证关系,另一方面精准把握了社会生产的内部区分,进而社会资本要实现再生产需要资本在内部设定差别,并通过资本内部要素之间的相互补充才能实现资本外化与收回这一辩证过程。中国人民大学刘志洪博士论述了资本逻辑的系统结构及其启示。他认为,以往的研究并没有对资本的逻辑形成足够的自觉意识,仍停留在“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他将资本运动所呈现的逻辑分为四个层次:总逻辑、核心逻辑、基本逻辑和具体逻辑。其中,总逻辑对应的是资本“所进行的总运动”,即在整体上展开为必然性地形成、扩张与扬弃的过程。核心逻辑是资本逻辑当中核心性内容,即价值增殖逻辑。在价值增殖逻辑的支配下,资本同时内含创造文明与消解文明这对相互矛盾的逻辑,即基本逻辑。从不同视角看,资本创造—消解文明的基本逻辑可以进一步分解为诸相互对立的具体逻辑,如提高效率逻辑与降低效率逻辑等具体逻辑。四个层次间内在联系与相互作用,使资本逻辑成为一个有机整体。
三、《资本论》研究与新时代经济
社会发展重大问题
面对当今社会发展出现的各种新问题,与会学者普遍认为《资本论》不仅没有过时,反而显得愈发重要,对《资本论》的研究有助于解决新时代的种种问题。
学者们对当今时代的垄断资本及其理论反思进行了考察。中共中央党校张雪琴博士探讨了垄断资本学派的凡勃伦思想渊源。她认为,凡勃伦从微观视角出发,揭示了垄断资本主义内在的痼疾,提出“破坏——不在场所有权”理论,以解释商业化、金融化对企业的控制,并提出“金融舵手”这一概念。之后的垄断学派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凡勃伦的观点,继续从经济的微观基础上对资本主义市场进行分析。她认为,对垄断学派与对凡勃伦思想的继承的考察以及他们对金融危机与“金融舵手”之间关系的考察,都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很大的帮助。
伴随着当今世界金融繁荣发展并在经济运行中逐步占据主导地位,金融资本对各部门形成了广泛渗透。中国人民大学马慎萧博士分析了工人家庭在资本强势推动中纳入金融化转型进程中的种种问题。她提出,虽然金融机制确实能给工人提供消费、住房、教育等等,但由此工人维持生存与生活的条件日益建立在金融体系之上。纯粹的金融资本循环并没创造剩余价值。金融利润的根源是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本质是对工人创造的价值的数次掠夺。
新时代的生产结构让传统的劳资关系发生了变化。对此中国人民大学齐昊博士认为,应该用“不稳定工作”的概念来完善传统的劳资关系理解。他认为,随着信息发展、新平台出现等时代变化,传统的雇佣关系发生了结构性转变,越来越多的人处于稳定工作与失业之间,即“不稳定工作”状态。《资本论》中讲机器大生产对传统家庭作坊的瓦解、妇女和儿童普遍参与劳动,可以看作是马克思对“不稳定工作”的探讨。传统经济学家在面对“刘易斯拐点”的时候往往会关注农村剩余劳动力,而《资本论》的启示让我们能更好地关注城市中的不稳定工作人口。
劳动力的再生产问题愈发成为当代经济学领域最紧迫的问题。清华大学硕士研究生牛子牛从两个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阐述:一是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愈发褪去了原有的强制性与惩罚性特征,而转变为资本对于自由创造性的情感知识劳动的寄生。二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兴起,使得劳动主体性问题再度置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中心。《资本论》的主体性构造理论提供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力再生产理论的基本参照,从这一基本参照出发,才能更为本质地思考资本主义的惩罚机制、意识形态、道德和科学话语等外部性或非外部性的劳动力再生产技术。
四、《资本论》研究与哲学、政治
经济学的对话融合
理论的创新既需要某一单一领域的深度挖掘,又需要研究者与研究者、领域与领域之间的对话与沟通。对《资本论》的研究能否取得创新性的学术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学者能否展开哲学、政治经济学的跨学科对话。学科的对话与交流,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固有属性,也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者推进学术创新的使命所在。不少学者围绕一些具体专题展开了哲学与政治经济学之间的互相阐释与对话。
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汇通,首先体现在如何理解《资本论》的科学性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庄忠正博士探讨了《资本论》在何种意义上是“科学”的问题。他分别从“科学”一词的复杂语义、从经济事实到社会现实、从政治经济学到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三方面展开分析。第一,马克思更多的是在德文词汇“Wissenschaft”的意义上界定科学概念的。所以在马克思这里,科学强调现实概念即本质与存在的自在自为的统一。这使得黑格尔式的思辨形而上学的基础上具有了实证性和批判性。第二,马克思引入辩证思维,将“感性具体”抽象为“经济事实”,又把“经济事实”上升为“社会现实”,于是赋予《资本论》更高意义上的科学性。第三,《资本论》的意图并不在于创立新的理论大厦,而是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所以马克思的目的不是“简单地确认一种经济事实”,而是“使现存世界革命化”。
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交融还体现在对价值形式论的辩证法意蕴的阐释之中。针对如何理解《资本论》中价值形式的辩证分析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杨洪源博士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货币形式辩证法进行了细致考察。第一,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货币章”中阐释的是商品“成为”货币的具体历史过程和具体现实过程,而非阐述概念间生成的必然性和概念发生史。第二,货币虽然产生于流通过程,但并不是“流通”本身的产物,而是以生产为起点的社会有机体的产物。第三,马克思认为,异化本身的发展“孕育着”消除它的可能性,异化的矛盾在经济层面上表现为经济危机,而人们消除危机就是试图克服全面异化。第四,货币形式的辩证运动并不会随着它获得作为货币本身的形式规定性而停止,货币作为离开简单流通并同这个流通相对立的独立物,是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这两种规定的否定的统一,从而表现为自我消灭的矛盾,并在流通之外完成向资本的过渡。
与会学者普遍认为,改革开放40年来,对《资本论》的深层次原著解读、理论研究与当代价值阐释都达到了新的高度,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共时性与历时性维度有了新的认识,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代意义与科学意蕴也有了新的理解。为了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及相关学科建设,就必须根植中国当代现实问题,以跨学科的总体性视域统摄多种研究范式。新时代的中国社会发展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基本原理的指引,更离不开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与《资本论》的持续对话。